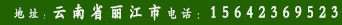|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主编:(美)梅维恒 译者:马小悟张治刘文楠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7 定价:.00 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可避免地在做方向相反的两件事:破解成见和制造偏见。如果你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是整齐划一的帝国统治产物,或者觉得儒家内部铁板一块,中国思想也只有儒释道三家,如果你坚持自古华夷两分,外族的“入侵”是一个单一的被“汉化”的过程——这也是等待着他们的必然命运,那么是时候读一读这本西方汉学界公认的中国文学史经典了。 已故北大教授季羡林在读过《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后,对主编梅维恒是这样评价的:“他的眼光开阔,看得远一些。我们不注意的一些东西,他注意到了。”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面描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各类景象,年代跨度自远古迄当代,且以世界文明史、文学史为参照,以国际化视野颠覆了传统研究模式。本书重在阐述中国文学中的议题,省略了不必要的原文征引,叙述流畅,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梅维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试读 选自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之引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美)梅维恒(VictorH.Mair) 文人文化的起源和影响 从隋朝(-)起,中国有文化的年轻人主要志向就是考取进士。拥有进士头衔,权力、地位和特权都会随之而来。进士头衔授予在京师会试中的及第者,表示他们在官僚体系中有资格获得一官半职。有时候,某位历史人物唯一可考的生平日期,就是他通过进士考试的年份。 为什么这一特定头衔在中国得到如此追捧?最简明扼要的回答就是,它表明了进士头衔拥有者具有读写文言文的最高级技能。这并不是对某人政治能力或者实践技能的考试,而是考察考生在文学写作(文章)方面的才能,所以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博士。连等级稍逊的秀才头衔(参加省一级的会试的必要条件)都被疯狂追捧,发须斑白的老人终其一生一次又一次参加,屡败屡战,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竞争激烈的考试是明经。地方官府会提名明经候选人进入每年的官职录用中。不过,进士考试强调的是文学写作,而明经则要求对经书的全面掌握。 科举考棚(广东,) 通过这些考试,等于向所有人宣布头衔的拥有者是书面汉语的精通者。这不啻为一项丰功伟绩,因为书面汉语非常难,必须要记诵大量文本。对科举考试的备考是一场旷日持久又艰巨的战役。因而,考生需要大量经济投入,通常只有来自富贵之家的子弟才能负担得起。 甚至在科举制度之前的西汉或者更早,拥有卓越文章技能的官员(比如博士)会得到高规格的尊敬。于是在古代中国,出色的文学能力会得到大量实惠,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约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能够拥有这一能力。士大夫人数的稀缺反过来又增添了他们头顶上的光环。逐渐地,一种以文章能力为中心的文人文化便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文的气质。 于是,要理解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生活,就必须把握文的意义和重要性。现代词典也许会对文这一词条给出如下定义:书写;文学写作;文章;文学;文化;文雅的;文化的;教育;文官(与武对应)。所有这些派生意义的根义是(美化的)模式,文便是所有审美上美化之物的总和,不过总体来说是和文学相关的。它构成了如下词汇:文化、文明、文艺、文学和文字等等。文尤其用来指称书写,特别是美文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几乎等同于文学。不过追寻文的深层起源,以期完全理解这一核心术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今的古文字学家在公认的最早的古汉字(约前年)中发现,文字像一个胸口有文身的人。这便使人有些不解,因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文身一般是与野蛮人和囚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青铜器时代的中国,文身是美好的象征。在许多人类早期文化中,文身都带有强烈的正面含义。比如在色雷斯人、塞西亚人和其他中亚民族,以及毛利人中间,文身是头领还有其他领导人的专属。实际上,文的基本意思在一个现在仍在使用的古老表达(即文身)中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殷墟甲骨文中的“文”字 从文身到(美化的)模式,再到文字、文章和文化,是一部漫长的发展史,而且从文身到文学、文化的演化太过彻底,所以根据文的起源几乎无法推演出其结果。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时代木乃伊身上,发现了像文字一样的E和S形状的文身。 不管青铜器时代的文身最终被证明是一种个人装饰还是一种公共书写,在中国历史中文变成了精英文化的核心特征。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心里清楚文的中心地位,习惯性地将它称为斯文(我们的这个文化),这句话出自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的《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文王之后,这是孔子夫子自道)不得与于斯文也。斯文被视为孔子及其先人--周王朝(约前-前)的开国君主--还有在这之前传说中的圣人流传下来的宝贵政治文化遗产。 欧内斯特·费内罗萨 中国文人文化中的文这一核心观念在西方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手里焕发了新的生命。最著名的是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stFnollosa,卒于年)就这一主题写了一部短小精悍却极具影响力的《汉字作为诗媒》(ThChinsWrittnCharactrasaMdiumforPotry;在其过世后的年首度出版)。庞德(EzraPound)和多位意象派诗人的创作受到这部作品的巨大启发。而该书的影响究竟是有害的(因为它对汉字的介绍是扭曲的)还是有益的(因为它将中国诗歌的基本概念介绍给西方诗人),评论家现在对此仍然聚讼不已。 书写对儒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儒家最典型的特征。儒家指的是拥护孔子之道的一派学者,最初活跃于战国时代(前/-前)。儒一词有儒雅、文弱以及温顺之意,实际上是这些词的同源词,也与有乳儿之意的字同源。儒产生于士阶层,实际上儒士这一全称表明了他们是特殊类型的士。士又是哪些人呢?在西周王朝(约前-前)初,士是像后世日本武士那样的武士,是早期封建社会中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在接下来的春秋(前-前/)和战国时期,士渐渐演变为后期封建社会中的学者阶层。成为士阶层主导的儒士,以其儒雅、文弱和温顺而著称,这既是一种讽刺,也颇具历史的吊诡。而孔子自己,是由武士一变而为文人的最佳例证。 作为武士的后裔,孔子肩负效力于军事的职责。实际上,他曾担任鲁昭公(在位时期:前-前)卫队的成员,但他的心思既不在御,也不在射(《论语·子罕》)。相反,他走向了一条政治游说的仕途。在鲁昭公针对实掌鲁国大权的公族季氏的秘密兵变失败之后,孔子益加坚定地选择了师这一角色,吸引了大批忠诚的门徒。他将自己所理解的先圣之道传授下去,整理编订包含先圣教导的古代典籍(包括《诗》和《易》),并致力于说服当政者采纳符合这些教导的政策。这确立了后世儒家对道德的重视,对经典的虔诚,以及对社会政治的入世态度。 儒家的经典文本并不是来自神启,所以并不能被视为宗教经文。对儒者而言,这些由孔子和其门徒所编纂的儒家经典所起的作用和宗教中的经文并无二致。正如经文在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中是权威的源泉,儒教经典也是儒家权威的源泉。在早期中国,书面文本受到极度敬畏,甚至书写本身也披上了权威的大氅。帝国政府的根基同书写技艺紧密交缠在一起。政府给士人文化以主导地位,这在具体的政府机构中可以窥得端倪。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有实际上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太学或者国子监。在这些学校,经过精挑细选得以入学的学生在各专某些经书的博士指导下就学。毕业后,年轻的学者们通常进入官员队伍,得到选派。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最具声望的学者通常被安置在翰林院中,翰林二字明显指涉了他们精湛的写作技能。翰林学士担负着为皇帝起草诏制的任务,他们经常--有的在翰林院任命的同时,有的在此之后--在帝国政府中身居要津,位极人臣。翰林院代表了仕途成功的顶峰,其唯一标志正是笔墨文章。 多样化的文类 传统中国文学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类别。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的《序》中,有以下分类: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碣、志以及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所有这些文学类型中,与官员的生活和活动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竟如此之多。政府官员生涯中使用的文类,还有一些未被萧统提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文章与官仕之间的紧密关系贯穿始终。因此,作家总是处于其作品要直接或间接地服从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需要的重重压力之下。纯文学或者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在中国出现得相当缓慢。直到佛教美学来临之后,文学的非实用主义方面才开始得到系统的欣赏、审视以及提倡。甚至到二十世纪中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文以载道的旧传统又在中国文学中再度抬头。论述文学在社会中担任的意识形态宣传角色,最著名的便是人尽皆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学的公共的实用主义使命和追求创造性表达的个人愿望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可以在赋的演变中得到展现。在文学语境中,赋最早是指《诗经》中的六种表达方式(赋、比、兴、风、雅、颂)之一。作为一种特定文学形式的赋形成于西汉晚期(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但是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能找到它的根柢,在西汉之后的数个世纪中,赋继续保持繁盛之势。 关于大夫(对高官的敬称)或者说君子,一句经常提到的话便是登高必赋。换句话说,当大夫或君子登上山之巅峰时,他必然情不自禁以一种美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登高必赋告诉我们,贤士不仅具有作赋的才华来表达自己崇高感受的能力,而且这么做也是环境使然。对于一位有修为的君子来说,从高处描述自己的所见近乎是一种责任。 然而在汉代,一些作家倾心于自身的描写才华,开始创作辞藻华丽的赋。(在沉郁冷静的人来看)他们的赋作辞藻铺陈,情感过度,手法夸饰,其因缺乏节制招致了不少批评。虽然这种新文学形式具有纯然之美感,但当时最知名的赋作家中至少有一位曾对自己的赋公开表示过羞愧。还有一些作者甚至在他们最出色作品的末尾加上否定自身的结语。但是,赋还是继续得到繁荣和发展,在六朝(-)重新勃兴,被运用到各种主题上(长啸、感怀、鹦鹉和雪等等)。到唐代,赋可以分为追溯到晋朝(-)的俗赋,以及音韵谐和、对偶工整的律赋。虽然旧的汉赋及其变体在唐代仍然间或有创作,但是总体而言赋已经衰落,在宋代(-)的文赋之后,赋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已经极少被采用。 简而言之,这就是赋这一文体在一千多年中从发轫到式微的波谲云诡的变化。要完全领略中国文学,需要全面把握从最讲究节律到最汪洋恣肆的各种文体。考察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类型,面对的是除了专家之外少有人知的一整个巨大文学宝藏,其富饶程度至今难以估量。比如,在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即约16-17世纪),有一种叫做小品文的文体曾盛极一时。小品文是中国文学数百种文体中的一种,对其一瞥,可以透过多种多样文体的棱镜管窥中国文学的不竭宝藏。 小品一词最早来自《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它是全译本二十四卷《大品般若波罗蜜经》的七卷本简译本。很明显,品是标准的佛教词汇,指的是章。刘义庆(-)在《世说新语》的文学(文与学)章三十四、四十三和四十五节中曾以小品来指称《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文学》中所记轶事大多与佛教有关,而我们在前文提到现代汉语中的文学是十九世纪经由日本对《世说新语》中文学(其根源来自《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的借译。因此,不仅小品具有很深的佛教背景,甚至五世纪浓郁的佛教氛围还催生了新的文学概念。不过,对晚明的小品当然不能仅仅通过早期佛教用法来理解。 小品难以用正式术语来描述其特征。小品若翻译成英文,在长度上从寥寥数句到三页或者多页不等。它们通常是非虚构的,不过有些作品却具有高度想象力。小品通常从头到尾都是散文,但掺杂韵文的情况也不少见。所有小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形式的非正式性。阅读小品,往往同阅读日本法师吉田兼好(约-约/)的《徒然草》(约)一般,虽然并不皆如后者那样麻痹自我。 最知名的小品作家有归有光(-)、陆树声(-)、徐渭(-)、李贽(-)、屠隆(-)、陈继儒(-)、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李留芳(-)、王思任(-)、谭元春(-)以及张岱(-约),其中尤以张岱最为突出。小品作家涉及的主题有战争、寺庙、观景楼、凉亭、草棚、学者、侍女、歌伎、演员、说书人、口技表演者、狗、书法、文房四宝、竹子、藤、乡村之旅、侍者、愚人、绘画、肖像、诗歌、退休、年老、死亡、梦境、童心、桃花、远足、溪水、湖泊、池塘、群山、饮酒,等等。阅读小品文集是赏心悦目的,它不仅使读者进入晚明的历史世界,更进入整个中国文学的恢弘景观中。 鲁迅书信 中国文学中的一些丰碑性作品,很难被严格归为定义清晰的特定文学类型,然而却因其具纪念意义的特质得到广泛认可。比如,许多传世书信,最初的读者只有收信人一位,但现在作为书信体文学而拥有无数读者。书信来自许多不同时代、地点和人物:司马迁(约前-约前85)的《报任安书》,解释了自己为何宁愿接受宫刑,而不选择自尽或者死刑,这样他便能接续父亲未尽的工作,完成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放浪形骸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告诉山涛为何自己决定与之决裂。诗人白居易(-)贬官南下,在江州给他三年未见的挚友元稹寄去《与元微之书》,凄凉深挚。中国人对字字珠玑、饱含感情的书信的这种偏爱,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像鲁迅(周树人,-)、陈寅恪(-)和胡适(-)这些文学界人士私人书信的公之于众所起到的作用,有的是激起学术争议,有的是解决学术争议。例如在苏轼(苏东坡,-)和袁枚(-)这样的名士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时事的评论、私事的吐露以及对各种主题(日常生活、亲族关系、道德或者政治倾向)的持续讨论。简而言之,中国作家在私人信件中袒露自己最私密的想法和感受。因此,许多书信之所以具有纪念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文字上的优美,更因为其中情感的完全敞露。书信在中国文学文化中占据崇高的地位,存世书信被编订成大量书信集,以供学生背诵和模仿。汉字里,信的提法有多种--书、笺、札、牍、尺牍、尺函、信,这不仅说明了书信的流行,而且说明了文学权威专家是如何严肃对待它的。 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剧的另一个醒目特征在于,同一材料在许多不同文类中会以文学语言或者白话语言的方式被再创作。清官包公破案便是其中用之不竭的一个主题。传奇性人物包公以历史上宋代官员包拯为原型,在各种故事和戏剧中成为正义的化身。 最后,中国文学的变化多端从其修辞性上可见一斑。虽然文人写作的曲笔表达是一种正常的修辞必要(见第四十三章),但是这一倾向在具体情境要求下往往会被秉笔直书所中和。大量与宫廷活动相关的文献(刘勰[约-]《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分类,如箴、诔和书--比如王安石[-]著名的万言书,康有为[-]向清光绪帝力论变法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上书),都是在不懈努力以求获得最大社会政治效应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在这些情况下,作者基本上不可能过于迂回曲折。并且,这一环境为政府监督的科举考试体系所不断强化,因为科举考试要求对具体主题进行程式化的遣词造句和文章结构。 汉代建立起来的经典注疏传统(见第四十四章)也加强了文官语境中对于清晰解释的追求。这里衍生了大量文类:注、疏、批、评、判、校、勘、解、释义、析等。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往往使注疏和评论(见第四十五、四十六章)泛滥,由此可见注疏冲动之广之深。无论从文类,还是从应用在各种文体上的注疏策略来看,中国文学都不是单声部的,相反,它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声部。 多样化的意识形态与人民 如果说中国有难以计数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修辞,那么它同样拥有丰富多彩的学说、民族和民间故事。有一种老生常谈,说中国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帝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属于同一民族,有着同一种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和习俗,等等,此种说法纯属谬误。中国的人口、社会和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多样性。即便是中国的精英社会和文化,也显示出高度的多样性。比如以思想体系为例,佛教和道教有着儒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浩繁经文。还有,儒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早在汉代以前(即公元前年以前),对于如何解读孔子思想,荀子(约前-约前)和孟子(前-前)之间就歧见迭出。而近两千年之后的新儒家中,朱熹(-)和王阳明(王守仁,-)的追随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激烈冲突,几乎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属于同一思想学派。(我们不否认某些人会提倡学说的一致性理想。虽然这些努力从未成功过,但它确实会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产生影响,使他们根据后来的思想,时代错置地解读前人思想,甚至添加附会。)另外,中国的思想光谱也绝不仅仅局限在佛教、道教和儒教,包括萨满教、法家、墨家、杨朱学说、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景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天主教、新教等在内的多种学说和实践,都曾在中国历史中或长或短地存在过。虽然这些思想派别并非都有宗师的世系更替以及权威的经典文本,却都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传统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一样,实际上由无限多的支脉和纤维构成,因此社会的整体纹理无论在结构还是在性质上,都是极其复杂的。 莫高窟笔画 这些学说立场以各种方式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文学。浸润了某一意识形态的碑文、诗歌、散文、故事、小说和戏剧,是很容易辨识出来的。佛教和道教是中国文学两种最丰沃的养分。仅仅说佛教和道教,就好像它们是泾渭分明的单一体,这种提法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佛教和道教各自有多种派别,更不用说大量的佛道合流了。有些宗派,如禅宗和净土宗是文学家和批评家特别丰富的文化资源。而道家思想天才庄子(前-前)对文学的影响则不可估量。仅试举一例,贾谊(前-前)的《鸟赋》是作者和创作日期都可以确定的最早一首赋。在这首作品全部四十四行中的九行(占六分之一)直接引用自庄子,而两行可以说来自《道德经》,另有一行同时出现在《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一部内容杂糅的道家著作)和《吕氏春秋》(公元前二世纪的一部法家汇编)中。庄子在后代作品中的回响不胜枚举。可以说,如果没有庄子,很难想象中国文学将会是怎样一副面貌。 虽然本书单辟两章(第九、十章)专论佛教和道教,但必须指出的是,将佛教和道教从过去两千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单独提取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因此,在本书各章中,都能找到佛教和道教的身影。专论佛道的两章主要处理宗教团体自身创作或翻译的经书。虽然这些作品卷帙浩繁,除了经文自身之外,还涵盖各种文本类型(传记、叙事和历史,等等),但也不可能穷尽佛教和道教的作用,以及它们对措词、意象、符号、结构、寓意方法、韵律特征还有一些全新文类和文体方面的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RolfStin,EdwardSchafr,KristofrSchippr,NathanSivin,AnnaSidl,MichlStrickmann,MichalSaso,IsabllRobint,JohnLagrwy,PaulKroll,LiviaKohn,StphnBoknkamp,KnnthDan,TrryKlman和LowllSkar等先驱学者已经给我们展示了道教这一变化万千的思维和信仰如何建构起了中国想象性作品的巨大框架。Schafr和Kroll的研究揭橥了大量中国诗歌中的道家维度。道教概念如仪式、炼金、养生和房中术对于中国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刻影响。近来学术界特别白癜风要怎么治疗好治疗白癜风中药方
|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一本打破你成见的
发布时间:2017-4-7 17:47:02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乡情莆田人不能不知道的8个世界第一
- 下一篇文章: CBA距揭幕战还有6天,精彩赛程奉上